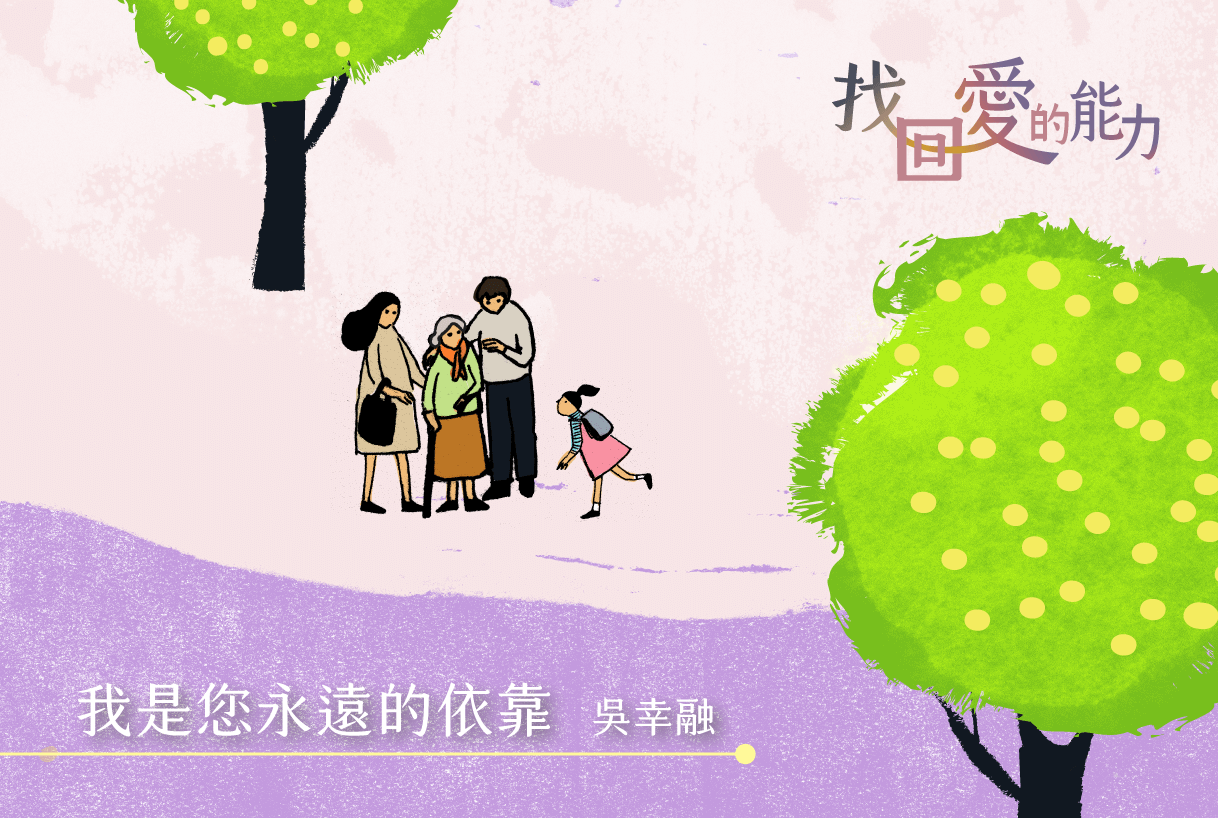本文節選自2017年4月29日的「日常老和尚學術研討會」演講內容,演講者為如法法師,主題為「四家合註譯著與日常師父志業」。本文標題、內文與圖片經福智文化編輯調整。
師父(編按:日常老和尚)的譯經事業不只弘揚了祖師譯經的精神,更使經典廣弘於僧眾與俗眾,擴大教法的影響力,若是從譯經事業的歷史來看,師父絕對是繼往開來、承先啟後的高僧,在譯經事業的貢獻上厥功甚偉。 |
從西元1111年,宋朝的譯場終結之後,具規模的譯場事業便宣告中斷,儘管漢地仍有譯師的出現,例如民國初年翻譯諸多經典的能海法師、法尊法師,已多為獨立運作。
經過幾百年的光陰,福智僧團決定重新啟建一套嚴密的譯場制度。1994年,師父開始招收沙彌、教習古文與藏文,為譯師的培訓奠定良好基礎;2014年,第一批學僧學完五大論,真如老師延續師父的志業,決定成立譯經院,也著手創立譯場的規章制度,始開創現今的大慈恩‧月光國際譯經院(以下簡稱月光譯經院)。
鉅細靡遺,完備譯場制度與規章
月光譯經院一共立出十六種譯場的職稱,比如授義師,專門指導譯師並裁決最後的爭論點;總監,掌控整個譯經的方向以及所有的規則;除此之外尚有主譯、主校、主潤、審譯、合校潤、語譯;還有參校異本的參異;考據所有典故及經論依據的考據;以及訓詁、核訂、眾校、眾潤、提疑、審閱。
上述十六種職稱,又可分成三大任務,第一是確定義理的準確性,所以必須由學畢五大論者來進行翻譯、審查,第二是行文的潤色,第三則是註解的工作。儘管譯場訂立之名目看似繁多,卻各司其職,在多方的管控下,才能確定經典翻譯的品質。儘管每次覆校還是會看到問題,但至少有一定的信心,不致於翻譯了五十萬字,沒有一篇敢發表的。
此外,譯場在翻譯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・四家合註》時,同時進行文言文與白話文兩個版本,一方面希望能承繼古代經典文字之優美,又能適應現代人的閱讀習性,這也是在這個時代才會發生,過去翻譯未曾有的形式。另外,譯經的同時,更針對讀者可能會看不懂的法義、出處、典故,進行了精細的註解,希望流通的時候,大家能夠更容易、順利地學習經典。

承先啟後,成辦譯經大業
月光譯經院發展至今,完全仰賴師父的遠見與睿智,因師父致力於弘揚圓滿教法,積極培養譯師,才有機會再現早已消失的譯場制度。譯經院的第一部譯著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・四家合註》,參與譯經的人員超過七十人,也就是說一部經典的翻譯和註解,必須要有七十位學僧和深具佛學素養的居士一起投入方能完成。若沒有師父早年奠立的地基,根本無法成辦如此殊勝的事業。
而月光譯經院有幾個不同以往譯場的特色:第一者是譯場建立的緣由。古代譯場大多由官方斥資、主持,因此只要官方不再投入,譯場便會嘎然而止,這也是為什麼譯場制度斷絕的主因。現在的時代,很難再有官方譯場的出現,於是師父聚集民間的力量,讓譯場重新誕生,既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譯場制度,卻又開展出不同的特點。
第二者則是譯師培養的方式。中國古代有不少關於譯經的論述,如彥琮法師提出「八備」,談一個譯師需要具足的素養、僧格,並提到要精通梵文、佛法的義理。師父承續了這樣的精神,在培養譯師時,除了佛法素養之外,也格外重視譯師的僧格的養成,以及文化、語言能力的具足。不同於歷史上的譯場多為個別培育,師父是以整個僧團為單位來教育。

第三者是註釋的完備。我們在譯經的同時,會把經典的註解同步、完善地寫出來。當然,註釋的完備並非譯經院首創,而我們仿效古代鳩摩羅什大師翻譯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作法,在譯經時同步完成經典的註解,記錄當時譯場的問答,也將討論的內容輯成經典的註釋。
另外,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──當經典翻譯完成,並不是單單書籍出版,然後收編進大藏經就結束了,而是努力弘揚,讓更多人一同學習。所以師父讓我們學習經典、翻譯經典的目標很明確,即是希望將來我們弘揚的,就是我們所翻譯的經典。每一本經典的問世,不只要有完善的翻譯、精美的編纂,更要積極推動大眾深學、廣學,因此每一部經典的問世,都意謂著有更多的人能夠真正地親近其中的內涵。
師父的譯經事業,既弘揚了祖師譯經、註釋的精神,又真正讓經典廣弘於僧俗二眾,擴大教法影響的局面,可以說是繼往開來、承先啟後的。
未來,將持續有一班又一班的學僧完成學業,不斷地投入譯經的隊伍之中,各項經典的翻譯計劃也將逐年開展,豐盈我們學習的經典。如今開始起步翻譯的經典,雖然僅是滄海一粟,卻也是譯經事業的巨輪啟動,祈願以此微薄的努力,奉獻生命於聖教,回報上師三寶的無上深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