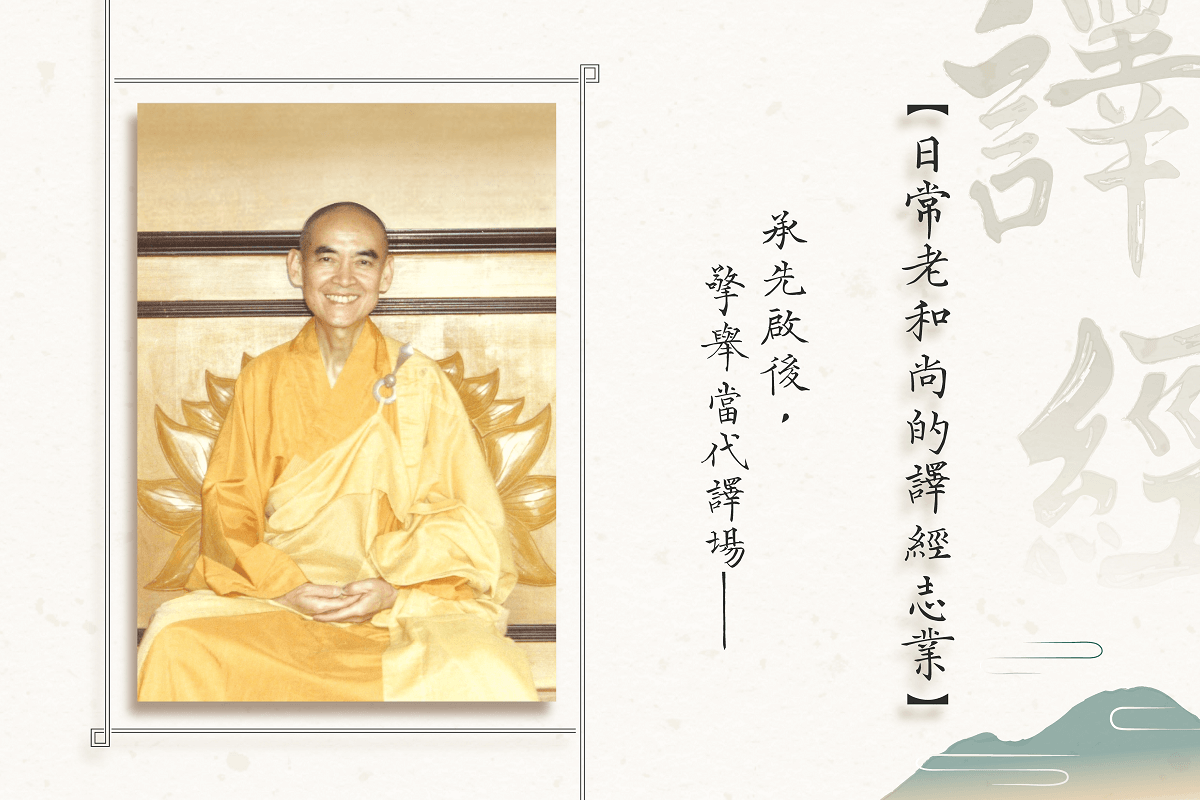鱉溪作為秀姑巒溪的支流,除了提供在地居民灌溉用水,還孕育了流域內多樣化的生態——「鱉溪」顧名思義,正因中華鱉在此地出沒而得名。除了鱉群,鱉溪還是臺灣特有魚種菊池氏細鯽,以及會從大海洄游至中上游產卵的日本禿頭鯊的棲息地。
然而,隨著當地的發展,鱉溪流域上的人造物也日漸增多,在短短16.91公里的河道上,足足造了23座攔河堰。儘管這些人造設施方便了人們取水灌溉,卻也攔腰斬斷了水生動物來往的路,更破壞了河川原有的生態。不論是難以尋覓棲息地的鱉群,或是當年隨處可見的菊池氏細鯽,還是再也無法回到上游產卵的日本禿頭鯊,曾經多樣化的生物群,漸漸在鱉溪絕跡。
跨域共學,放下身段聆聽在地聲音
為了讓鱉群重回鱉溪,管轄鱉溪流域的水利署第九河川局曾在2018年規劃了3000萬的預算,以「鱉稻共生」作為方向,預期在鱉溪實行環境營造工程。在規劃即將定案之時,第九河川局向當地居民舉辦了一場說明會,然而由於環境工程的設計過於人工化,這項計劃並未得到民眾的支持,甚至擔憂會否進一步破壞鱉溪已經嚴峻的生態環境。

當時剛上任的第九河川局局長謝明昌看到了居民的疑慮,因而決定叫停環境營造工程。被問及制定好的計劃案全盤推翻、一切程序得從頭來過,九河局會不會覺得是一個艱難的決定?謝明昌局長如此說到:「在規劃階段多花時間沒有關係,只有在初期和民眾達成共識,後續執行才會順暢。」
在與當地居民的溝通中,九河局瞭解到其實民間已經凝聚了一股力量,想要改變鱉溪、為她盡一分力,對於鱉溪的未來也有許多具建設性的想法。謝明昌局長提到,政策不能只是從上以下地執行,必須與民眾充分溝通,才能讓政策切實和順利地實行。因此在鱉溪的治理上,九河局決定採用公部門和民間團體合作共治的模式,藉由成立各有關部門與民間跨域共學的溝通平台,相互討論、彼此傾聽,以在各方的想法中找出對鱉溪最好的共識。
TIMOLAN生態園區,從13到3000的努力
經過與居民多番深入的交流後,鱉溪復育計劃制定了四個目標:還石於河、還水於河、還地於河、還魚於河。鱉溪的左岸有一塊高灘地,在復育計劃的過程中被徵收。九河局與在地民眾研討過各種可能性,最後決定循「還魚於河」的方向,將這塊高灘地改造為保種復育基地,並命名為「TIMOLAN生態復育區」。「TIMOLAN」源自阿美族的語言,意為「低窪之地」。

園區以復育菊池氏細鯽作為目標,在地方推動鱉溪復育主力張振岳老師的協助下,規劃了三個生態池,分別為復育幼魚的復育池、放置成魚觀察的保種池,以及預防外來種因大水蔓延進入其餘兩池的控制池。
生態園區規劃完成,萬事俱備,卻缺乏了最重要的一項要素——復育需要的種魚,但在鱉溪裡卻找不到足夠合適的菊池氏細鯽作為種魚。謝明昌局長回憶當時的情況:「民間團體在鱉溪找了好久,也只能找到三尾。」所幸張振岳老師後來找到嘉義大學的賴弘智教授,他們早期在鱉溪採集過魚種,而對方也相當慷慨地送出一部分菊池氏細鯽用於復育工作。
經過多方不懈的努力,TIMOLAN復育園區收穫了豐碩的成果,最初復育區內只有13尾菊池氏細鯽,而如今的數量已經超過3000尾。
公部門下放資源,由共治向自治的鱉溪
鱉溪復育工作的成功,河川局對於這種公部門與民間合作的模式大力肯定,因此也逐步將這樣的策略擴展到其他河川流域的治理上,例如後來馬佛溪、木瓜溪等河川的治理計畫。而考量到人力、相關投入資源的限制,第九河川局也正計畫逐步撤出已然獲取一定階段性成果的鱉溪計畫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部門又如何確保鱉溪日後的治理能繼續維持?對此謝明昌局長強調,公部門往後的角色會從主導者轉換成支援者,退居二線,然而並不代表完全撤出鱉溪流域的治理,河川局與民間團體在此前的合作中所建立的溝通管道,仍然會維持聯繫。
鱉溪復育雖以「還石於河、還水於河、還地於河、還魚於河」四部曲作為階段目標,但復育工作最終希望能「還溪於民」,將鱉溪歸還給在地社區。因此在官民合作的過程中,也公部門也持續協助民間團體熟悉治理程序,以及掌握可連結的資源等,藉此強化在地的力量,使鱉溪復育從「共治」順利走向「自治」。
鱉溪復育並非朝夕之事,唯有攜手能成功
鱉溪的復育工作自2018年開始,到今天已經走過了四個年頭。對於第九河川局最初定下的「四還」目標,都已順利地達成了——曾經被搜刮一空的大石頭,重新回歸到鱉溪的河床上;上游的污染源頭得到解決,讓鱉溪的水能再次孕育生命;在攔河堰修築人工魚道,也終於能讓魚群重新踏上被切斷已久的洄游之路。
雖然鱉溪的復育工作取得了纍纍成果,然而河川復育並非一年、兩年就能達成,鱉溪要真正回復到以往的樣貌,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。不過只要所有人仍然懷著一顆為鱉溪盡一分力的心,相信假以時日,鱉溪必定能再度成為那條生機勃勃的母親河。

封面照片提供:天賜糧源公司